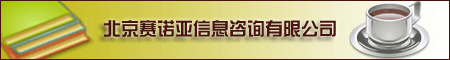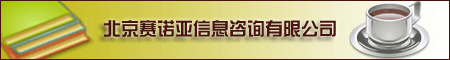·公司收购的价值争论与立法取向(1)
四、 公司收购的司法审查 —— 以反收购措施为中心
以公开收购要约为主要形式的敌意收购和一般善意收购的首要区别就在于收购和并购的敌意性质,发盘者“越过管理层的头顶”与目标公司的股东接触,最终改组后者的管理结构、改变其经营策略。据在美国的统计,在被兼并之后 3 年内有半数目标公司经理失去了职位, [153] 而失去职位即意味着丢掉丰厚的薪水和分红、优厚的福利待遇和受人尊敬的稳定职业,而这些都是管理层无法接受的“噩梦”,所以毫不奇怪他们会竭力进行抵抗。 [154] 可以说,收购市场白热化正是发盘者和目标公司管理层之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相互斗法的结果。 [155] 在紧张激烈的收购攻防战中,公司股东(特别是目标公司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的利益如何保护,无疑是各国立法面临的重大课题,但实际情况变化万端,仅靠立法远远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法院由此肩负起维护公平和效率的重任。 [156]
(一)美国法院的司法审查
在美国, 80 年代以后花样迭出的反收购措施有效遏制了收购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而失败的发盘者或因溢价未能实现而愤愤不平的股东常常会对管理层采取的防御措施提起诉讼,其诉由通常是管理层违反《威廉姆斯法案》或违反忠实义务。但在此问题上,美国法院大都采取保守态度,以“商业判断规则” [157] 作为保障管理层自由决策的依据。在 Panter v. Marshall Field & Co. [158] 这一典型案例中,法院即援引商业判断和善意推断规则,认定目标公司为反并购而采取的扩张战略合法。但本案少数派法官 Cudahy 认为,在利益严重冲突的反收购活动中不能适用商业判断规则,本案中的目标公司董事显而易见违反了受托责任( fiduciary duty )。
由于美国有众多的巨型公司在特拉华州注册,该州制定的法规和州最高法院的判决是现代美国公司法的基本法律渊源。 [159] 从 Unocal 、 Moran 到 Revlon ,短短的一年之内,特州最高法院完成了塑造 80 年代后期收购活动的案例“三部曲”。 [160]
在 Unocal v. Mesa Petroleum Co., 一案 [161] 中, Mesa 公司提出先后以等值的现金和垃圾证券分二阶段收购 Unocal 公司,作为防御 Unocal 宣布了一项“毒药丸”策略: [162] 一旦 Mesa 取得其 50% 以上的股份,则所有除 Mesa 及其关联人士以外的 Unocal 股东均有权以较高的作价向公司换取信用等级较高的债券,从而使 Mesa 的收购企图成为泡影。特州最高法院认为:公司董事有受托责任为股东的最大利益服务,董事的谨慎义务 (duty of care) 还包括保护公司及其股东免受来自某些其他股东的潜在损害,但董事的上述职权不是绝对的,因为他们无权纯为或主要为稳固自己的地位而采取激烈的防御手段。所以一项意在阻碍收购企图的防御性措施必须从股东的利益出发,不得有任何诈欺或其它不当行为。以上述标准衡量, Unocal 董事的防御措施是合理与适当的,并和董事确保少数股东得到公平作价的责任相符。在特州法院的上述判决之后不久,美国联邦证券与交易委员会( SEC )也颁布一项 14d-10 规则, [163] 要求公开收购要约应以相同的条件向同一证券等级的所有证券持有人作出,以体现“不偏向任何一方的中立立场”。但同时,特州法院也表明目标公司管理层的自保行为 (entrenchment) 是应当禁止的,在 Schnell v. Chris-craft Industries, Inc., 案 [164] 中,法院判定,被告公司管理层试图利用公司机制和特州法律来剥夺公司股东征求委托权的合法权利,而此目的是不正当的,和已确立的公司民主原则不符。在 Aprahamian v. HBO & Co., 案 [165] 中,董事会在得知一名心怀不满的股东已经成功地取得了大量投票委托权后决定更改股东年会的举行时间,法院宣布此种行为无效。在 Blasius Indus., Inc. v. Atlas Corp., 案 [166] 中,法院禁止目标公司为防御收购而在在交错任期的董事会 [167] 中增加两名新的成员。在 Hubbard v. Hollywood Park Realty Enter., Inc., 案 [168] 中,法院表示:修改章程细则以使董事候选人名单必须在股东大会开会前先经过管理层的行为不得在收购攻防战中不当使用。
在 Moran v. Household Int ’ l., Inc. [169] 一案中,特州最高法院维持衡平法院的判决,认为 Household Int ’ l., Inc. 为应付潜在的收购威胁而采取的“优先股购买权计划” (the Preferred Share Purchase Rights Plan) (该计划规定股东在公司面临收购的情况下,有权以每股 100 美元的价格购买发盘者每股价值 200 美元的股票)是董事会在收集情报、与顾问及投资银行家进行广泛讨论的基础上,为免受可能的强制性、粉碎性( bust-up )公开收购而基于商业判断规则所作的合理措施,该措施并不妨碍 Household Int ’ l., Inc. 股东对公开收购要约作出承诺。法院并且指出,本案中 Household Int ’ l., Inc. 董事会不是对现实存在的收购进行抵抗,而是对潜在的收购威胁预先准备防御措施,但这并不导致董事会丧失商业判断规则的保护。法院同时承认,对董事会防御行动的合法性不能一概而论,而要视情况逐案进行具体分析。
在另一个重要案例 Revlon, Inc. v. MacAndrews & Forbes Holdings, Inc., [170] 中, Pantry Pride 公司敌意收购 Revlon 公司的全部股票, Revlon 先后采取部分回购股份、发行“毒药丸”的方式进行防御,最后则求助于“白衣骑士” Forstman Little & Co., ,并向该公司提供价格优惠的锁定资产 (asset lockup) 。 Pantry Pride 闻讯进一步将要约价格提高到超过 Forstman 的出价,条件是 Revlon 撤消“毒药丸”及财产的锁定,但 Revlon 不为所动,坚持与 Forstman 的合并, Pantry Pride 遂起诉至法院。特州最高法院首先肯定 Revlon 第一阶段防御的合法性受商业判断规则的保护,紧接着认为当董事由收购的防守方变为在 Pantry Pride 和 Forstman 中间寻求一个最佳出价的“拍卖人”时,其职责即发生了变化,为驱逐一个敌意发盘者而进行有偏向的交易不再是适当的行为,董事应当为股东的利益而寻求一个最高的出价。 Revlon 的董事不顾竞价要约的事实而和 Forstman 订立财产锁定协议即违反了忠实义务。鉴于 Revlon 辨称其行为是为了保护包括“毒药丸”单据持有人在内的利益相关者,法院指出虽然在某些情况下此种考虑有其合理性,但董事会仍应以公司股东利益为最终关怀。作为特州最高法院反收购案例“三部曲”的最后一章, Revlon 案表明法院认为( 1 )目标公司管理层为防御敌意收购而采取的措施一般而言会受到商业判断规则的保护; [171] ( 2 )但是在目标公司的被收购和分解已是不可避免时,管理层的首要使命是为公司股东寻找可能情况下的最高出价,而不应主要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得失。 [172] [173]
但是在数年以后的另一重要案例 Paramount Communication Inc. v. Time Inc. [174] 中,特州最高法院又把 Relvon 的原则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之内。 Time Inc. 与 Warner Communications, Inc. 已就一个以股易股的合并计划达成一致, Warner 将作为合并以后的存续方。 Paramount 出人意料地提出一项针对 Time 全部发行在外股票的现金收购要约,并最终将收购价提高到 200 美元 / 股(公开收购要约提出时 Time 股票的市场价为 126 美元 / 股),并且要约的有效期截止日定在股东就 Time-Warner 合并进行表决之前。 Time-Warner 宣称它们之间的合并给股东带来的远期收益将超过 Paramount 的要约出价,并修改合并计划,使 Time 可以立即以 70 美元 / 股的价格收购 Warner 51% 的股票,稍后再以价值 70 美元 / 股的现金和股票收购其余 49% 的 Warner 股票。 由于此项出价将使 Time 负起 70-100 亿美元的巨额融资债务,而 Time 原有的良好负债结构正是 Time-Warner 合并的基础之一, Paramount 迅速提起诉讼,要求禁止 Time-Warner 合并。特州最高法院维持衡平法院的判决,认为本案与 Relvon 案的区别在于 Time 董事会并未面临一项“粉碎性”敌意收购,其所作所为只是普通的防御而非对公司法律人格的抛弃,所以 Relvon 案的原则不应适用, Time 可以完成和 Warner 的合并。法院由此表明无意将 Relvon 案的原则适用于仅仅是“参与收购” (in play) 或“公开出售” (up for sale) 的公司。特州最高法院的此项判决受到普遍批评,因为合并以后的 Time-Warner 业绩不佳,到 1993 年年底, Time-Warner 股票的市价仍未达到 1989 年 Paramount 出价的 200 美元;学者更严厉指出,该项判决允许目标公司管理层以“战略发展计划”为借口逃避不受其欢迎的收购要约,从而“使对收购的司法审查发生了决定性转变而明显地向在职管理层倾斜”。 [175]
有意思的是,在 Paramount Communication Inc. 与 Time Inc. 之间的争议发生之后两年, Paramount Communication Inc. 自己也成为收购的目标。 1993 年夏天 Paramount 开始和 Viacom,Inc. 就合并事宜进行谈判, 9 月 12 日双方签订了锁定性的合并协议, [176] 为避免触发 Paramount 章程中反收购的的“毒丸”条款,协议规定该项条款将作相应修改。但另一家公司 QVC Network, Inc. 几乎同时发出了对 Paramount 的收购要约,几番争夺, Viacom 把总出价提高到 93 亿美元,但仍比 QVC 的出价少 13 亿美元。这时, Paramount 宣布接受 Viacom 的要约,并修改“毒丸”条款以防止 QVC 的要约得到接受。衡平法院 [177] 和特州最高法院 [178] 一致认为 Paramount 和 Viacom 拟议中的合并涉及 Paramount 控制权的转让,显而易见类似于 Revlon 中的情况,根据 Revlon 和特州的其它判例, Paramount 至少应该考虑 QVC 的出价。特州最高法院的此种见解使 Viacom 和 QVC 对 Paramount 控制权的争夺战持续了两个月, Viacom 才最终取得了胜利。由此人们开始反思特州最高法院的此一最新判例如何限制了两年以前 Time-Warner 判例的效力, Coffee 教授指出:“ Paramount 案表示特州最高法院已经从 Time-Warner 案的立场上退后了半步——即不再坚持只有对目标公司的分解或清算才导致目标公司的管理层有展开‘拍卖’的责任”,他认为是否应当适用 Revlon 原则取决于是否有一新的控股股东参加收购竞价。 [179]
特拉华州的判例法表明: [180]
1 、 目标公司可以采取任何措施来预防收购的威胁,这些措施包括规定董事的交错任期(使发盘者难以建立自己的董事会),发行只有较少的表决权的股票(使发盘者即使大量持股也不能对公司实施控制),规定“超级多数”条款(合并要发盘者以外的表决权中的绝大多数同意方能通过)或“公平价格规则”(两阶段收购中后一阶段的收购价必须等同于前一阶段的收购价),发行“毒药丸”证券(当发盘者掌握了目标公司一定比例以上的股份后,另外的证券持有人即可以低价买进公司的其它股份,借以“稀释”发盘者的持股;或可导致发盘者手中的股份自动稀释)。只要符合“商业判断规则”的要求,目标公司董事会采取的上述策略都可得到法律的保护。
2 、 当收购要约已经发出,目标公司管理层应特别谨慎并在采取对应措施时从公司的利益出发。但在管理层维持与第三方的合并计划、高价从发盘者以外的股东处回购股票、向承诺支持管理层的第三方发行证券、提起阻止收购的诉讼时,法院常常表示出极大的宽容。
3 、 只有在管理层决定“拍卖公司”时,法院才愿意对其行为加以约束。这时,目标公司应当回赎“毒药丸”证券、避免“锁定式”交易。这时,各发盘者机会均等,以使目标公司股东获得可能情况下最高的溢价。
这样,尽管美国法院明确表示禁止目标公司管理层纯为或主要为稳固自己的地位而采取激烈的防御手段( Unocal v. Mesa Petroleum Co., ),但对反收购规制的软弱无力,实际上使管理层可以放心大胆地实施反收购措施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181]
(二)英国法院的司法审查
在英国,《收购与兼并城市法典》基本原则之 9 规定,目标公司董事会在签订任何协议之前必须进行认真的考量,以免董事会在未来对股东提出建议的自由受到限制。但尤其在竞价要约的场合,董事会究竟是否有权签订锁定式( lock-out ) 协议仍是一悬而未决的问题。在 1980 年代以来的 4 个主要案例中法院试图解答这一问题: [182]
Heron International Ltd. v. Lord Grade 案 [183] 涉及对一家广播公司的收购,该公司董事持有超过 50% 的有表决权股份,并且公司章程第 29 条规定转让任何股份都需得到董事会的同意。董事会先向发盘者 A 承诺无条件接受其要约,但发盘者 B 随后又以较高的出价提出收购。在对有关的争议作出判决时,上诉法院( the Court of Appeal )指出:“当董事决定被收购符合公司的最大利益而又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发盘者时,拥有章程第 29 条那样的权力的董事的唯一职责即是去寻求最高的出价。除非董事相信某一发盘者已经提出可能情况下的最佳出价,否则他们不应承诺向该发盘者转让他们自己的股份。在董事必须在敌对的发盘者中间作出决定时,公司的利益只能解释为现有股东的利益”。董事会因此被指令寻求专家意见和收购与兼并委员会的帮助,以考虑是否接受 B 的要约。
在 Re A company 案 [184] 中,法官 Hoffmann J. 的观点有所不同。该案情节与 Heron 案基本相同,只是目标公司是一家小型的私公司( private company ),一小股东诉称他在收购活动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Hoffmann J. 说:“我不认为董事会必须承担在其权利范围内建议和采取一切措施去寻求最佳出价的义务。在本案中,董事就他们自己的股份行使作为股东的无可质疑的权利去接受较低的出价要约,并且因可以理解和完全披露的理由而希望其他股东中的大多数也将接受此项要约,那么对我而言,要说他们有接受较高出价的义务是不自然的。”
在一个稍晚的案例 Crowther Group plc. v. Carpets International plc [185] 中,法官 Vinelott J. 认为目标公司给予发盘者的承诺通常应被视为包含一项隐含的条件,即“如果”没有更好的出价出现。对于那些认为“只要一项锁定协议已签订,就不会有更好的要约,因为对‘更好’的要约的承诺将给公司带来得不偿失的违约责任”的观点, Vinelott J 决定不予采信。
近期的一个案例 Dawson International plc v. Coats Patons [186] 中, Coats Patons 与 Dawson International 决定合并, Coats 并且同意合并将被宣布为善意合并, Coats 的董事将不寻找或鼓励其他的要约或和其他的发盘者合作,董事就其所持股份接受要约并将建议公司的其他股东也同样接受要约。 Dawson 和 Coats 还就合并事宜联合发出了书面声明。但 Viyella 同 Coats 接触,表示无论 Dawson 出价如何其均有意以更优的出价收购 Coats ,并从后者的财务顾问处得到了有关 Dawson 出价的详情,最终与 Coats 达成了新的合并协议。 Dawson 遂提起诉讼。法官 Lord Prosser 提出,当人们在依城市法典进行公司收购时,他们所作的声明或订立的协议通常只是他们在自律性的城市法典项下对目前意向的说明,并不构成具有法律强制性的合同约束(但这不妨碍在违反城市法典的原则或规则时受到收购与兼并委员会的处罚),法官由此判决 Coast 没有违反任何合同义务并驳回了原告的起诉。
通过以上 4 个案例至少可以看出,英国法院并不摈弃收购中的竞价,而是鼓励和促成竞价的发生,并且认为当有更好的出价时,原有的锁定协议通常即自行失效,这从某种程度上符合经济效益的原则。
五、 公司收购的经济分析及其评价
进入 1990 年代以来,曾经狼烟四起的美国收购市场上敌意收购的事例急剧减少。据统计, 1988 年全美共有 27 桩敌意兼并,涉及金额 385 亿美元; [187] 1991 年只有 2 桩敌意兼并,涉及金额 7740 万美元; [188] 到 1992 年则根本没有一位敌意发盘者顺利完成收购。 [189] 学者认为“收购战争已经结束,在职管理层取得了胜利”,随着敌意收购的不复存在,股东们已经不能奢望在惩诫或去除无效率的管理层方面能得到来自资本市场的帮助。由于投票委托权争夺已被证明对管理层没有很大的威慑作用,那么只有经营不善、破产清算的风险才能惩罚无所顾忌的管理层,而当产品市场上的此种风险变成现实时,公司和股东已经遭受了成百万甚至数亿元的损失。 [190]
造成敌意收购几近消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的经济因素是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美国金融市场发生重大变化,信用紧张,垃圾债券市场崩溃,用于收购的巨额资金难以筹措。 [191] 但无可否认,目标公司采用的“毒药丸”策略和美国各州反收购立法及法院的保守态度是更深层次的原因。 [192]
经济分析法学者认为公司收购尤其是敌意收购是有益的,发盘者通过自己的经营努力使目标公司实现较优的业绩,从中获取目标公司股票的差价收入,并在客观上起到了监督公司在职管理层的作用;目标公司股东获得溢价收入,并由于收购市场的存在而“免费”获取了公司的外部治理环境;从社会总体而言,效率得以提高、价值得以增加;唯一受损的是低效的公司在职管理层,他们被无情的市场规律撵出了“经理帝国”,因此对发盘者或公司收购满怀敌意。经济分析法学者对敌意收购案例大幅减少的现象十分忧虑,对此种现象背后的立法及司法原因则大加鞭挞。
经济分析法学者的主要观点集中在关于公司收购的合同理论、竞价理论和限制管理层理论上。
(一)经济分析法学有关公司收购的合同理论
经济分析法学的基本观点是:公司即合同,公司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合同法。 [193] 有一种论点认为,公司在职管理层作为公司——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应该有权对收购要约采取各种应对方法,只受制于对其权力的合同约束,法院的工作则应限于监督和强制合同的履行。 [194] 按照这种思路,一个公司可能奉行对收购敬而远之的“独立”政策,让在职管理层可以有时间来制订和实现有利于公司的长远政策,或许奉行独立政策的公司的管理层更有可能为公司寻求最佳的合并条件。那么持独立政策的公司的此种选择应当和持“开放”政策(即对收购持欢迎态度)的公司的选择一样受到尊重。另一方面,公司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组织为投资者准备了各种各样的投资渠道并就此展开竞争,鼓励或限制收购也是公司竞争的方面之一,竞争中的优胜者将会生存、发展。如果某一公司采用的反收购政策不利于投资者,其股票价格即会下挫,结果将使该公司成为更吸引人的收购目标。所以是否采取、采取何种反收购措施的决定权尽可交给公司在职管理层,市场自然会对他们的行为有无效率作出评判。
此种结论虽然有一定吸引力,但却是建立在“完全自由的市场”假设之上的,所谓“完全自由的市场”至少要求:( 1 )公司作为合同必须是合法的;( 2 )合同必须稳定且能以较低成本来履行或强制执行;( 3 )违约现象能够观察并可以得到补救;( 4 )有关某个公司运营的合同应对其它公司没有影响。而实际上所有这些前提是否真实都是值得分析的。 [195]
首先,公司中各方当事人的合同自由受到政策与法律的限制。股东和公司及公司管理层签订了合同,但这并不影响股东选择时机与价位来出售其手中所持股份的自由。 [196] 股东可行使合同上规定的“空仓期权” (puts) , [197] 即在一定情况下将股票回售给公司或第三人的权利 [198] ;股东亦可出卖其股权的“行使选择权” (calls ) , [199] 即给予潜在的发盘者在将来以一定的价格取得股份的权利。如果发盘者相信目标公司的股票市价应该高于购买选择权的价格,但实际上却低于后者,那么他就会购买该项选择权。在理想的市场和合同机制下,发盘者应当可以随意“采购”他所感兴趣的目标股份的行使选择权。但事实上,各国立法都不允许发盘者随时、随意发起公司收购,相反,美国的《威廉姆斯法案》、英国的《收购与兼并城市法典》和我国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中规定的信息公开制度和公平价格原则等等,都剥夺了发盘者一些最有力的收购武器,即收购的突然性和迅速性。
即使公司的合同机制不受法律约束,其在现实生活中也会受到一些限制。债券持有人和公司雇员等固定的剩余权益索取者 (holders of fixed residual claims) 的权利义务可以在有关合同中详细进行规定,但对公司股东──非固定的剩余权益索取者 (holders of non-fixed residual claims) ——而言,试图在合同中详尽规定权益即使不是不现实也是成本极其高昂的,所以股东只能靠赋予管理层受托责任 (fiduciary duties) [200] 的方式、通过代理关系 (agency relations) [201] 来得到保护。正是代理责任和变更管理层的有效机制的结合使管理层拥有作出“商业判断”的广泛权利,而对于股东保留的更换管理层这一最基本的和不可让与的“天赋”权利,管理层是无权擅自加以剥夺的,笔者相信,这也正是英国《收购与兼并城市法典》中规定“当一个‘真正的’要约已向目标公司管理层发出时,或当目标公司或其管理层有理由相信一个要约已经迫在眉睫时,未经股东大会批准,管理层不得采取任何行为以使要约遭受挫折或使股东丧失自己作出决定的机会” [202] 等限制管理层行为的条款的原因。
在职管理层通常在公司章程中设置“毒药丸”等反收购条款, [203] 但这些条款大多是在公司公开发行上市之后增补的。公司的合同理论认为,各方当事人在缔结公司这一合同、发行股票并上市时要经过市场的考验,如果公司章程中有不利于股东的或效率低下的条款,发起人将不得不咽下发行价低迷的苦果。但在发行成功以后、公司存续期间添加的章程条款是没有经过市场测试的,由于股份公司股东的分散性和被动性,在职管理层提出的此类反收购修正案并不难通过股东大会的审查;偶尔遭遇机构投资者的反对意见时,管理层则大可使用“商业判断规则”保护伞,采用不需通过股东大会的防御方案,其结果是管理层违背股东的真实意愿、规避了市场机制、牺牲了公司和社会的效益。
即使合同条款的设立完全合理合法,享有充分信息的在职管理层也肯定在收购攻防战中占尽优势。如果有合同说:在面对收购要约时公司管理层应当主持“拍卖”,以使股东获得最佳的出价,那么管理层完全能够用苛刻的“标底”来吓退或用延长拍卖时间来拖垮潜在的发盘者。由于信息的非对称性,股东很难分辨管理层是在延长拍卖期以促使竞价发盘者提高出价还是在掘濠自保 (entrench) 。而由于利益冲突和“道德风险” (moral hazard) 现象的不可避免,后一种可能性是大量存在的。
总之,公司法的经济分析理论认为公司是包括股东和管理层在内的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协议或合同,但因为该合同中的反收购条款先天不足(未通过市场测试,不能反映股东的真实意愿)、欠缺公平(发盘者和在职管理层因为政策法律原因而力量不均,股东和管理层之间则有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现象等问题),股东完全有理由行使自己的天赋权利,通过收购市场来更换不称职的管理层。
(二)经济分析法学有关公司收购的竞价理论
是否可以允许目标公司管理层采取措施以鼓励竞价收购并使股东获得较高的溢价?公司法的经济分析理论持否定态度。 Easterbrook 和 Fishel 认为任何一种反收购的防御措施都将给投资者造成损害,因为它们使收购活动利润减少从而其发生频率也随之下降。发盘者之间的竞价同样使收购的成本增加、利润减少,使潜在发盘者和收购市场客观上作为公司的外部治理环境的激励受挫。举例来说,某目标公司的股票市价为 50 元,假设一个发盘者有信心在收购以后将其市价提高到 100 元,他只要出价 60 元就可以顺利完成对该公司的收购(从而净赚 40 元),但是如果目标公司的管理层顽固抵抗并最终使收购变成若干家发盘者之间的“出价比赛”,那么第一个发盘者很可能要出价至少 95 元才能实现收购(只能至多赚 5 元)。从短时间来看,此类竞价的确增加了目标公司股东的收益(所得每股溢价从 10 元提高到 45 元);但从长远来看,很少会有人再去冒风险发起收购运动,外来的监督机制由此减弱,代理成本升高,股东(无论是现有目标公司的股东还是全社会所有公司的股东)的整体利益也随之受损。
竞价对于参加竞争的发盘者而言也是不公平的。头一个发盘者花费时间与精力去发现与确定合适的目标,后来者却只要花费小得多的成本就可以加入到竞争行列中,很明显第一个发盘者的沉淀成本不易得到补偿。“如果当第二要比当第一合算的话,外来监督就会减少了”。 [204]
(三)限制目标公司管理层理论
公司法的经济分析理论认为公司收购是限制合同成本的机制,换言之,收购降低了监督和更换在职管理层的成本或管理层的代理成本,在创造私人价值(发盘者的差价收入和股东的溢价收入)的同时也创造了社会价值(社会效益的提高)。与此相对应,成功的反收购措施使这些价值无法取得,甚至产出负效益,所以法律应当强制管理层对收购保持中立和被动,让股东自己决定是否出卖手中所持股票, [205] 这样才能产出社会的最佳效益。由此,经济分析法学家对美国法(尤其是各州判例法)持强烈的否定态度。
(四)简短的评价
收购(尤其是敌意收购)的确是本世纪西方经济史上最具争议性的现象之一,对它应该采取何种态度,是限制、禁止还是放任、鼓励?论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206] 各国立法者似乎也犹豫不定。 [207] 经济分析法学者绕开苍白空洞的道德、伦理说教,率先从经济效率的视角对公司收购进行审视,辅之以经验研究成果,得出了一些颇具启示性的结论,如突破目标公司股东与管理层之间合同的樊篱,以真正的合同论作为鼓励收购的理论基础;提出充分认识收购的积极意义,对目标公司管理层的反抗行为进行限制,以及对美国各州反收购立法的严厉批评等等,都是值得参考的有益见解。但是,经济分析法学者对于收购竞价的分析,则有可以商榷之处。
Lucian Bebchuk 在他的系列研究论文中指出收购竞价并不一定附生反收购措施的诸多消极作用。 [208] 首先,发盘者的沉淀成本 (sunk cost) [209] 并不是如此之大,而且可能因其所持有的目标公司股票升值而得以消弭;然后,竞价使目标公司的控制权转移到能最有创造性地使用它的人手中,这本身就使效率得到了提升;第三,如同发盘者寻找目标一样,事实上目标公司也在寻找合适的发盘者,允许其发起竞价、自我拍卖,有助于提高其寻找发盘者的激励,由此补足“头一个发盘者”损失的激励。对于上述种种,经济分析法学者尚不能作出有力的解释或反驳。从现有的数据来看,是否有竞价的确与目标公司股东所能获取的溢价有正相关关系;而同时有几个发盘者的收购比较仅有一个发盘者的收购确能产生更高的溢价;竞价使目标公司股东获得高于一般收购 4%-6% 的溢价收入;当竞价一直持续到“中标者”最终成功收购公司时,则会有高达 17% 的收入;但若竞价的结果是所有的发盘者都知难而退时,即会产生净损失。 [210] 当然,由于竞价引起股东溢价增加的数额是否一定超过因为潜在发盘者的激励减少而带来的损失?这仍是一个需要长期的经验研究才能解答的问题, [211] 但万千上市公司股东潜在和现实的溢价收益毕竟是立法者无论如何不该忽视的── 因此竞价似乎应该受到鼓励。
六、 对我国公司收购立法的几点建议
(一)我国收购立法的特点
我国证券交易市场在 1990 年代初建立以来, [212] 已有数起收购案例出现, [213] 但是真正具备敌意收购特点的,却似乎只有发生于 1993 年 9-11 月的宝安收购延中事件 [214] 和 1998 年 6-11 月的大港油田入主爱使股份事件。 [215] 敌意收购的事例几近于无,意味着我国上市公司的股东缺乏公司治理外部环境的保护。究其原因,除了由于历史上的因素,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仍分为国家股、法人股、外资股与社会公众股,而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股和法人股或者不流动或者限制流动,对上市公司的公开市场内收购只能从为数不多的社会公众股着手, [216] 以至形成颇具中国特色的“收购概念股” [217] 现象以外,有关法规的严厉规定也是造成敌意收购“难得一见”的重要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章“公司合并、分立”对于公司合并只有简单的 3 个条文,即第 182 条(公司合并应由公司股东会作出决定)、第 183 条(股份有限公司合并必须经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和第 184 条(公司合并的形式和程序)。但对上市公司的接管与收购,则需遵照 1993 年 4 月 22 日国务院发布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条例》(以下简称“股票条例”)和中国证监会根据股票条例制订的《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试行)》(以下简称“信息披露细则”)的规定。
股票条例第四章“上市公司的收购”是规范我国公司收购活动的首要法规规范,在和英国及香港地区类似的规定如信息披露制度(第 47 条 1 款、第 49 条)、同等收购条件制度(第 50 条)及比例收购制度(第 51 条 3 款)之外,其主要特色为:
1 、 限制个人收购上市公司。第 46 条规定“任何个人不得持有一个上市公司 5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超过的部分,由公司在征得证监会同意后,按照原买入价格和市场价格中较低的一种价格收购。”但“外国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个人持有的公司发行的人民币特种股票和在境外发行的股票,不受前款规定的 5 ‰的限制。”
2 、 限制公司收购的速度。第 47 条第 2 、 3 款:“任何法人持有一个上市公司 5%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后,其持有该种股票的增减变化每达到该种股票发行在外总额的 2% 时,应当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向该公司、证券交易场所和证监会作出书面报告并公告。” [218] “法人在依照前两款规定作出报告并公告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和作出报告前,不得再行直接或者间接买入或者卖出该种股票。” [219]
3 、 禁止取得控股权的部分要约,限制强制要约的价格和付款方式,后者即所谓“收购价格法定主义”。第 48 条:“发起人以外的任何法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达到 30% 时,应当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 45 个工作日内,向该公司所有股票持有人发出收购要约,按照下列价格中较高的一种价格,以货币付款方式购买股票:(一)以收购要约发出前 12 个月内收购要约人购买该种股票所支付的最高价格;(二)在收购要约发出前 30 个工作日内该种股票的平均市场价格。” [220]
4 、 规定较长的要约期间。第 49 条第 2 款:“收购要约的有效期不得少于 30 个工作日,自收购要约发出之日起计算。自收购要约发出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收购要约人不得撤回其收购要约。” [221] 第 52 条 2 款:“收购要约人在要约期内及要约期满后 30 个工作日内,不得以要约规定以外的任何条件购买该种股票。”又实际上延长了要约的期限。
5 、 规定要约预受的无条件撤回权。第 52 条 3 款:“预受收购要约的受要约人有权在收购要约失效前撤回对该要约的预受。” [222]
6 、 单方面规定剩余股份的强制出售权。第 51 条 4 款:“收购要约期满,收购要约人持有的股票达到该公司股票总数的 90% 时,其余股东有权以同等条件向收购要约人强制出售其股票。”但对同样情况下,收购要约人是否有权要求其余股东向其出售股票则无规定。 [223]
7 、 规定严厉的“收购失败”制度。第 51 条 1 款:“收购要约期满,收购要约人持有的普通股未达到该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总数的 50% 的,为收购失败,收购要约人除发出新的收购要约外,其以后每年购买的该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不得超过该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总数的 5% 。” [224]
(二)评价及几点建议
股票条例 1993 年 4 月发布时我国证券市场诞生未久,沪、深两个证券交易所和第一批上市公司刚刚出现,立法者洞烛上市公司收购将会关系收购与被收购者双方及各自股东、证券市场上的其他投资者的重大利益,未雨绸缪,预先订立法规以作规范,对证券市场的法制建设贡献良多。但立法工作正如 199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 Coase )所说,“一旦考虑到进行市场交易的成本,那么显然只有这种调整(笔者按:指法律对权利的直接调整或法律确认的对权利的调整)后的产值增长多于它所带来的成本时,权利的调整才能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的运行效率产生影响。” [225] 从美国各州 1980 年代末的反收购立法(包括判例法)在敌意收购由盛到衰的过程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我们已经看到此种影响力是如何的巨大,那么,立法者在完成国民所赋予的“立规矩以定方圆”的重大使命时,就“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以追求法律效率为己任,手持天平、脚踏实地,小心谨慎地衡量各种法律调整方案带来的产值增量与它所附生的成本之间的关系,从中选择投入社会成本最少而产出社会效益最多者作为立法的模本。
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证明,公司收购惩诫无效率的目标公司管理层、为目标公司股东带来溢价、给发盘者及其股东带来差价收入,由此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其积极作用不容忽视。在我国,公司管理层对于股东的受托责任或代理责任尚未在法律上得到明确界定,为公司股东维持一个外在的监督机制即显得尤为重要,而有效的公司收购市场正好能提供这样的机制,所以立法的基本取向应是基本肯定公司收购作为公司外部治理环境对于保护投资者利益和优化配置资源的重要作用,在确保基本公平(信息公开、 [226] 竞价自由 [227] )的前提下,鼓励收购并适当放松管制、限制目标公司管理层的防御行为。 [228]
就一些具体问题,笔者试提出几点建议:
1 、 关于增加持股的时间限制
股票条例第 47 条对于任何法人( 1 )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达到 5% ;及( 2 )在达到 5% 之后其持有该种股票的增减变化每达到该种股票发行在外总额的 2% 时的信息披露义务,即继续收购节奏的控制作出了规定,业界内俗称“公开 + 慢走”规则。“《条例》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在对此规则进行解释时,反复强调“在几种利益之间找寻一个均衡点”,即: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及保护企业(发行人)的利益的均衡;保障中小股东获取充足信息的权利与不过分限制收购市场的均衡;对大股东一次买入的股票数量进行限制和不进行限制两种原则之间的均衡。 [229] 诚然,“公开”原则对于保证证券市场上的基本公正,对于维护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是极为重要的。但根据“慢走”规则,希望从证券市场上吸纳目标公司股份以达到收购目的的发盘者,从持有前者 5% 发行在外的普通股(构成书面报告和公告义务)到持有 29.99% 的该等股份(尚未构成强制全面收购义务)而取得目标公司的控制权, [230] 至少需要 39 个工作日的漫长时间。 [231] 在此期间,发盘者还要总共 13 次向目标公司、证券交易场所和中国证监会作出书面报告并且按照证监会制定的准则规定的内容和格式将有关情况刊登在至少一种证监会指定的全国性报刊上。 [232] 不难想见,单考虑股票市场上目标公司股价的自然和人为的上涨因素,收购的巨大成本都是任何一个发盘者所无法负担的。仅此一条,发盘者通过集中竞价的证券交易系统来进行收购的道路即被堵塞,“均衡”也就无从谈起。至于“慢走”规则的其它原因,“目前我国通讯传播及市场分析系统均不够发达” 的状况已有所改观, [233] “大部分投资者对市场上的价格动态不够敏感” 则并不是中国证券市场投资者独有的特点, [234] 所以“慢走”的规定是到了应该取消的时候了。 [235]
2 、 有关强制全面收购义务
根据股票条例第 48 条规定,持有一个上市公司 30% 以上股票的股东必须在该事实发生后 45 个工作日内向该公司所有股东以特定价格发出全面收购要约。强制全面收购使发盘者无法策划对目标公司的部分收购,为收购不得不背上筹集巨额资金的沉重包袱,增加了公司收购的成本,学者并批评为“介入私法自治,颇有可议”。 [236] 赞成者则认为作此规定是贯彻公平原则的需要。 [237] 但是一者,现代公司制度中已有保护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成熟体系, [238] 英美判例法更明确宣示大股东对小股东的受托责任, [239] 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可有较为充分的保障;二者,证券法上的“公平”原则应有其确定的含义和适用范围,不应将其作极端化的理解,一般而言,只有当大股东滥用资本多数决或其优势地位时,小股东方有请求大股东以公正价格收购其所持有股份的权利。 [240] 再者,如果所有得不到经营管理权的小股东都有强制出卖股票的“公平”权利,那么我国现有绝大多数上市公司的社会公众股股东是否都有同样的权利把股票出卖给占控股地位的国有股股东?或者,控股权人发生变化的公司中的小股东都有权把股份强制出卖给新的控股股东?由此可见,强制全面收购制度的存废确有可以商榷之处。实际上,强制收购在世界范围内也主要是英国和原属英殖民地的香港地区才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并没有相应的制度; [241] 欧洲共同体有关公开收购的公司法第 13 号指令草案虽然规定了强制收购,但又允许发盘者可以在 7 种情况下免除该项义务,欧共体会员国监督机关还可视实际情况,在上述种情况之外免除发盘者强制收购的义务。 [242] [243]
3 、 有关目标公司管理层的职责
在公司收购过程中,目标公司管理层经常处于利益冲突的焦点:一方面,管理层是应对目标公司效率低下负责的中心,是发盘者往往计划更换(从而在客观上惩诫)的经理团队;另一方面,管理层又是目标公司现行经营管理活动的中枢,负有让公司股东免受损害的受托责任。不能排除管理层会利用手中的职权抵制收购活动,从而给股东带来损失,所以有必要在收购攻防战的激烈争斗中明确规定目标公司管理层的职责。在此方面,英国《收购与兼并城市法典》的规定值得借鉴:该法典规则 3.1 指出,目标公司管理层有义务就任何收购要约征得足够独立的专业建议, [244] 并且该种建议的实质内容必须通知股东;遇有管理层收购和控股股东收购的情形时,独立建议尤其重要。城市法典基本原则第 7 条规定,当一个“真正的” (Bona fide ) 要约已向目标公司管理层发出时,或当目标公司或其管理层有理由相信一个要约已经迫在眉睫时,未经股东大会批准,管理层不得采取任何行为以使要约遭受挫折或使股东丧失自己作出决定的机会;第 9 条规定,发盘者和目标公司的董事在建议其各自的股东如何行事时,必须总是从其作为董事的职守出发而不得考虑其个人或家庭的持股……(目标)公司的股东在发出任何可能影响其在未来对股东作出建议的能力的承诺之前应该进行仔细的考量,(因为)该等承诺可能激化利益冲突及造成董事对其受托责任的违反。香港公司收购及合并守则也有类似规定, [245] 该守则并且对目标公司董事局未经股东常会通过不得采取的行动做了细密规定, [246] 欧洲共同体公司法第 13 号指令草案中亦然。 [247]
至于股票条例第 46 条限制个人收购上市公司的规定,则显而易见违背股东平等原则(法人股东和自然人股东平等、内国股东和海外股东平等),操作起来难度极大,在立法技术上也有可议之处。 [248] 究其根源,可能还是 1992 年 5 月 15 日国家体改委发布的《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中对于自然人充当股份公司发起人的禁止性规定。 [249] 但此一规定已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生效而废止, [250] 既然公司法取消这一限制是“顺应时势、尊重现实”的措施, [251] 那么股票条例第 46 条的修正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公司收购的价值争论与立法取向(1) |